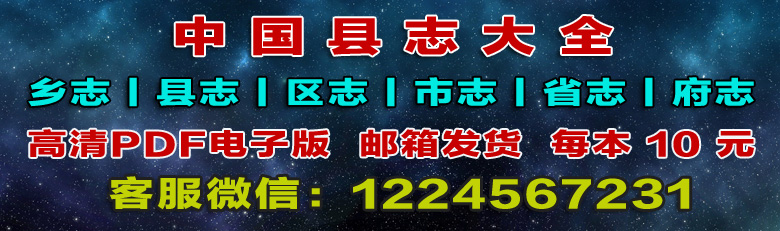顺治丁亥科常州五进士与方志编修
发布时间:2019-01-31 点击数:2813
顺治丁亥殿试开清代常州进士科甲之先河,众多进士都曾主政一方并主持修志。加强清初科举进士及其修志之举的综合研究,不但可以探析特殊历史背景下进士群体丰富复杂的人文精神世界,更可以从其修志行为之中,洞悉毗陵文化传统在这一群体中的润泽与传承,并为今人修志提供诸多启示。
五进士与方志编修
冯达道,字惇五,号鹭蓉,武进东乡五牧十里堡人(今横林余巷),顺治丁亥科二甲第39名。历官户部云南司主事、江西司员外郎、福建司郎中、辛卯顺天乡试同考官、钦差督理清江浒墅关务,任陕西汉中府知府,升任山西河东转运使。诰授中宪大夫,晋授中议大夫。所至皆有政声,重视地方文献,其中顺治十三年修成《汉中府志》6卷、康熙十一年修成《重修河东运司志》10卷,两志均有自序,现北京图书馆有藏。
季芷,字兰如、兰儒,号介庵,武进人,顺治丁亥科三甲第26名。历任福建福州府理刑推官、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康熙八年任直隶任县知县,十二年修成《任县志》12卷,有自序。国家图书馆现藏有康熙十二年刻本的康熙间增刻本。
吴守寀,字含章,武进人,顺治丁亥科三甲第100名。历任湖广房山知县、江西金溪知县、行人司行人、河南杞县知县、江西瑞州知府,康熙八年七月任山西乡试副主考。顺治十六年修成《杞县志》,未刊,康熙三十二年知县李继烈再修县志时稿本犹存,大约于乾隆十一年再修县志时稿本已佚。据曾参与该志纂修的何彝光在康熙三十二年再修《杞县志》时所撰志序中回忆称:“余时曾预其事,得失盖目击之,大旨荒落,未为完书”,李继烈也在再修志志序中称其“中间抵牾时存,鱼豕相半”。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康熙三十二年刊孤本。
徐可先,字声服,号梅坡,顺治丁亥科三甲第112名,武进小留人。历任直隶束鹿县知县、龙泉县知县、庆元县知县、山东登州府知府、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河间府知府、山东提督学政按察使司副使。顺治十二年春修成《龙泉县志》10卷,今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七年刻本苏遇龙修《龙泉县志》,该志是在顺治县志基础上参考众志修成,并收有徐可先原序。顺治十七年7月编订修成《登州府志》,同年10月由其倡导并参与编修、招远知县张作砺主修的《招远县志》4册10卷修成,徐可先有序;前者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三年刊本、任璿修《登州府志》收有徐可先撰顺治志序,后者国家图书馆有藏。康熙十七年编订《河间府志》10册22卷,徐可先撰有序言,今国家图书馆有藏。康熙十九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及继任格尔古德纂修《畿辅通志》,徐可先也参与了该志的纂修。
史树骏,字光庭,号庸庵,顺治丁亥科三甲第191名。历任直隶河间府宁津县知县、兵部职方及清吏司郎中、河间知府、顺德知府、肇庆知府。康熙十二年主修《肇庆府志》32卷;由马元与释真朴撰修,康熙十一年刊刻的《重修曹溪通志》,史树骏为其撰有志序。
通过对五进士所修方志的审读,特别是从各方志的编修体例及自撰序言、凡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对方志的价值定位,以及对编修实务的深刻认知,而在这背后,我们还可以体察到在朝代兴亡、政权更迭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顺治初年常州进士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常州士人“尚德、尚文、尚学”的文化传统。
1.方志定位背后体现出自觉的史鉴意识
五进士编修方志共11部。观诸历史,顺治朝大部分时间忙于政权的巩固,对方志的修撰并不十分重视,直到顺治十七年才出现了第一部省编通志即由贾汉复修、沈荃纂的50卷本《河南通志》。而官方大规模倡导修志行动直到康熙十一年,由保和殿大学士卫周柞上书建议参照河南、陕西两省通志,在全国推广通志纂修并被康熙采纳。二十二年康熙命礼部檄催各省上交通志。因此结合修志时间及志序看,五进士的修志行动,大多体现出一种明显的自觉意识。
从方志文本来看,这种自觉与他们对方志的定位及其背后强烈的史鉴意识密切相关。它来自于毗陵士子对“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史书功能的自觉接受与传承,而这既是中国史学著述的治学传统在方志中的再现,也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在方志中的映射。冯达道、史树骏及徐可先正是这方面践行的典型。
冯达道在顺治十三年的《汉中府志》志序中就清晰辨析了方志的价值,即面对“户口”“赋役”“兵防”“地貌”“建置”动态的“变”的特点,志则在于“纪变也”。作者以一个高级地方官员和学者的眼界,指出了方志在服务为政者备治一方时所具备的的参考与指导价值:“备考而谨书之,使良庖司割者知大窽坚软所在,砉然游刃诊脉,而志其浮沉虚实、据案处方补泻,可以无误。志之利益如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在志序中冯达道还融合了自己十多年来对时世变化,尤其是历经战乱、民生不易的感悟,对后来继修府志者提出了“有与立计、有与定心、有与为提呼”的期望。史树骏也在《肇庆府志》志序中喊出了“盛衰之端,莫非政治”。这样的感触对于顺治初年的进士群体,绝不是一种空洞感叹,而是有着深刻的人生体验与现实的兴衰警示。
相对于冯达道等,徐可先的这种自觉意识更为明显。他在顺治十二年《龙泉县志》自序中,首先回忆了初到任时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景象,并与旧志中记载的繁华安定形成强烈比照,进而指出“读是志者,取旧新以考互,俯仰曩今,低徊兴废固知”。在调任登州知府后,“涖登逾月,輙询旧志”,在所修的府志自序中开篇即称:“善为治者,在审其急而先图焉,能裨军国则为之,能益民生则为之”,并结合当时的一统大业及登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指明方志所具有的“俾当事有所取鉴”、“援昔证今”的特殊价值。在其所作《招远县志》志序中史鉴意识更趋明显:“求所以、示褒讥、昭美剌,惟邑乘是赖,则纂修之役,乌容不汲汲欤?”。及至康熙十七年主修《河间府志》则更明确地在志序中强调志的价值:“志其地、志其地所生之人、志其地所贡之赋、志其人与地所被之政治”,并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指出“政治得失,后之志今,如今之志昔,伊可怀哉,洵可畏也”。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史鉴自觉意识并不仅仅来源于史学及儒教传统,还与科举有着关联。科举取士至明清时已趋完善,进士更是科举人才中的佼佼者,尤其进士乃是经殿试考定,而殿试则是联系实务与时势开考制策,又称“时务策”,它较好的体现了举子对儒家经义的融通能力以及面对实际的经世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方志的定位认识,及其在编修中的实际体现,也是对进士能力综合检视的延伸。
2.方志编修之中体现出精到的实务认知
五进士不仅对方志的定位中体现出自觉的史鉴意识,而且在具体的编修实务方面,也都有着精到的认知和总结。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志书体例的设计上,还体现在对修志难易的深刻认识以及修志人员的精心选聘上。
就体例设计而言,五进士颇费苦心。冯达道所修《新修河东运司志》虽名为运司志,但却体例完备,全书十卷,旁搜广辑,卷一为图考、建置、星野、山川、城池、盐池、渠堰,卷二为盐法,卷三为制救、监临、职官、宦迹,卷四则为学校、师儒、选举、秩祀、风俗、武备、灾祥,卷五为帝王、名贤一,卷六为名贤二、阔德、流寓,卷七为疏议,卷八、卷九为文苑一,卷十为诗赋,除前三卷直接与河运、盐业有关,其余则可以视为对当时社会风貌的广泛记录,同时还附图七幅,可谓是对运城叙论最为详尽的一部志书;而其编修的《汉中府志》,康熙二十八年汉中知府滕天绶重修府志时尽管评价冯志“篇章虽云典雅,而搜罗未免简略”,但滕氏在编纂体例上却是“仍旧志之条目,缀后来之考订”,可见其体例设计的合理。季芷在《任县志》“凡例”中首先提出:“志当分品类,视其重轻以为先后”、“其间节目又以类相从”,而从其对条目排序的阐述中可以窥见严谨的逻辑顺序;而在“官师志”中对续增的人物事迹,则注重对碑碣资料的使用且宁缺毋滥,同时在“人物志”中坚持入选之人“品必协乎公好,论比洽乎舆情”,“不能曲徇揄扬以秽信史”,也即是强调人物事迹的实证性、人物品评的客观性。如此种种,皆为的见。徐可先参修的《招远县志》在其凡例中则明示:“凡引古必载出某书,以见考据”、“宦迹、人物,必考诸国史,据其家乘,参以公议,示有征兼论定也。若见在者,恐涉贡谀,概不敢赞一辞”,这实际是对方志编修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但也更大程度地确保了方志内容的可靠性与可检索性。史树骏曾在肇庆本地人梁应时处得到崇祯版府志并借阅,后在康熙十七年编修府志时对崇祯版旧志体例提出了批评:“大约鏊之成书喜为标目,有表、有传、有纪、有志,议论虽多,考核未尽,事多舛互,编次失伦。所收艺文半于卷帙,未免滥觞之议”,这就提出了方志编修中的“如实记述”、“详尽考核”与“评点议论”间如何科学取舍、合理平衡的命题。而所有方志中设立的诸如“孝友”、“选举”、“乡贤”、“节义”等条目,则更具有典型的价值传导特征。
相对于体例优化设计,冯达道与季芷还从理论的层面对修志的诸多挑战进行了总结。冯达道在《新修河东运司志》中提出修志有“三易”、“四难”,“三易”包括“天子不称制以断,宰执不秉笔以裁,挠掣无人,注涂在我,一易也;地迩则边幅,有所必循,职专而搜讨,不容旁猎,条例显设,编摩夙成,二易也;营私无斗米之乞,畏咎无百口之忧,参考传闻,使垂实录,三易也”,“四难”则为“敬慎之难”、“详核之难”、“审定之难”、“裁制之难”。次年,季芷在《任县志》自序中则从五个方面,即文献的征集、学识的优劣、资金的筹集、文字的表达、评价的客观,既生动又具体地阐述了方志编修的“五难”。二人所述,皆为要领,且为的见。
与清代中后期修志略有差异的是,五进士在纂修人员的选择上除在职官员外,缙绅生员的选择往往别具意味,既有对其史才见识切合修志需要的考虑,更似有借助修志这一文化工程,从心理上消弭汉族缙绅对异族统治抵触情绪的努力,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顺治朝方志的编修中。典型的如顺治十六年吴守寀主持《杞县志》编修,编修人员何彝光,字叔献,康熙二十五年选贡,康熙三十二年曾再次参与县志编修。其兄何印光乃明末举人,却在北京投奔了李自成起义军;弟弟何胤光,崇祯癸未馆选的36名庶吉士之一,李自成攻陷北京被俘,复仕大顺政权,故被清代史家计六奇、谈迁分别于《明季北略》卷22、《国榷》卷100中列入“从逆诸臣”或“降臣”。但作为这样一个家庭中的一员,何彝光却被吴守寀邀请加入方志编修,且在该志人物志、艺文志中收有其家族成员的传记及艺文作品多篇。
通过对五进士所修方志的仔细研读,联系当今方志编纂中出现或面临的诸多问题及挑战,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1.继续坚持方志的史籍地位,重新彰显方志的史鉴价值
当今修志,往往注重历史事件或事实的简洁陈述,条目设置也相对简单,但缺乏内在的逻辑延伸与支撑,以及积极必要的价值传导,整个方志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单纯性档案记录特征,从而忽略了方志应有的为当下、为后人提供历史“批判性理解与借鉴”的功能。因此,从方志编修初衷及价值理念传达的角度,我们要向前人求智慧。
2.结合方志编修具体实务,积极促进史述史鉴的有机融合
冯达道、季芷对于方志编修难易的精到阐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社会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今人修志所拥有的便利条件与古人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因此,当今修志更需要在具体实务中努力做好资金的稳妥安排、人员的精心选聘、体例的科学设计以及材料的海量选审、行文的恰当表达,而对于后者,更应当努力坚持和追求“崇实、精审、文畅、扬善”的原则。
参 考:
[1]王新命、薛柱斗统修《江南通志》卷四十四“人物?皇清”,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2]清王其淦、吴康寿修《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二“人物?宦绩?国朝”,清光绪五年刻本。
[3]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6册进士冯钟岱会试朱卷“履历”之“六世祖达道”,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1月印行。
[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宫内阁大库档案119562-001、104053-001、089364-001、089099-001、086690-001。
[5]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32册卷206《诰授中宪大夫直隶河间府知府升山东提督学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级梅溪徐府君墓志铭》,清代传记丛刊158册综录类07,台湾明文书局1985版。
[6]《清圣祖实录》卷30“康熙八年秋七月。壬辰朔”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
[7]李周望纂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大清顺治四年进士题名碑录丁亥科》,《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三册“大清顺治四年进士题名碑录丁亥科”,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清光绪三十年本《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1969年12月第1版。
[8]滕天绶、严如熤辑《汉南续修郡志》卷一“旧志序”所录顺治丙申萸饮之日冯达道所撰《汉南府志序》、康熙己巳九月滕天绶所作府志序,国家图书馆藏民国13~14年翻刻嘉庆十八年刊本。
[9]冯达道修、张应征续修《新修河东运司志》卷一“序”,康熙十一年刻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0]季芷修《任县志》,国家图书馆馆藏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刻版康熙间增刻本。
[11]卢思诚、冯寿镜修《江阴县志》卷14“选举?甲科”,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四年刻本。
[12]《杞县志》(12册24卷)卷9“职官志?国朝?吴守寀”,国家图书馆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13]苏遇龙修《龙泉县志》,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12]徐可先修《河间府志》,国家图书馆康熙十七年刻本。
[13]张作砺修《招远县志》,国家图书馆顺治十七年刻本。
[14]任璿修《登州府志》,国家图书馆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15]屠英修《肇庆府志》,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二年重刻道光十三年刻本。
[16]史致卓等修《常州史氏族谱?九溪公二分》,光绪十九年常州东门德馨祠板。
[17]尹继善统修《江南通志》,国家图书馆乾隆元年刻本。
[18]马元、释真朴撰修《曹溪通志》,康熙十一年刻本,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
[19]郝玉麟统修《广东通志》卷29“职官?国朝?肇庆知府”,国家图书馆雍正九年刻本。
五进士与方志编修
冯达道,字惇五,号鹭蓉,武进东乡五牧十里堡人(今横林余巷),顺治丁亥科二甲第39名。历官户部云南司主事、江西司员外郎、福建司郎中、辛卯顺天乡试同考官、钦差督理清江浒墅关务,任陕西汉中府知府,升任山西河东转运使。诰授中宪大夫,晋授中议大夫。所至皆有政声,重视地方文献,其中顺治十三年修成《汉中府志》6卷、康熙十一年修成《重修河东运司志》10卷,两志均有自序,现北京图书馆有藏。
季芷,字兰如、兰儒,号介庵,武进人,顺治丁亥科三甲第26名。历任福建福州府理刑推官、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康熙八年任直隶任县知县,十二年修成《任县志》12卷,有自序。国家图书馆现藏有康熙十二年刻本的康熙间增刻本。
吴守寀,字含章,武进人,顺治丁亥科三甲第100名。历任湖广房山知县、江西金溪知县、行人司行人、河南杞县知县、江西瑞州知府,康熙八年七月任山西乡试副主考。顺治十六年修成《杞县志》,未刊,康熙三十二年知县李继烈再修县志时稿本犹存,大约于乾隆十一年再修县志时稿本已佚。据曾参与该志纂修的何彝光在康熙三十二年再修《杞县志》时所撰志序中回忆称:“余时曾预其事,得失盖目击之,大旨荒落,未为完书”,李继烈也在再修志志序中称其“中间抵牾时存,鱼豕相半”。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康熙三十二年刊孤本。
徐可先,字声服,号梅坡,顺治丁亥科三甲第112名,武进小留人。历任直隶束鹿县知县、龙泉县知县、庆元县知县、山东登州府知府、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河间府知府、山东提督学政按察使司副使。顺治十二年春修成《龙泉县志》10卷,今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七年刻本苏遇龙修《龙泉县志》,该志是在顺治县志基础上参考众志修成,并收有徐可先原序。顺治十七年7月编订修成《登州府志》,同年10月由其倡导并参与编修、招远知县张作砺主修的《招远县志》4册10卷修成,徐可先有序;前者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三年刊本、任璿修《登州府志》收有徐可先撰顺治志序,后者国家图书馆有藏。康熙十七年编订《河间府志》10册22卷,徐可先撰有序言,今国家图书馆有藏。康熙十九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及继任格尔古德纂修《畿辅通志》,徐可先也参与了该志的纂修。
史树骏,字光庭,号庸庵,顺治丁亥科三甲第191名。历任直隶河间府宁津县知县、兵部职方及清吏司郎中、河间知府、顺德知府、肇庆知府。康熙十二年主修《肇庆府志》32卷;由马元与释真朴撰修,康熙十一年刊刻的《重修曹溪通志》,史树骏为其撰有志序。
通过对五进士所修方志的审读,特别是从各方志的编修体例及自撰序言、凡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对方志的价值定位,以及对编修实务的深刻认知,而在这背后,我们还可以体察到在朝代兴亡、政权更迭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顺治初年常州进士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常州士人“尚德、尚文、尚学”的文化传统。
1.方志定位背后体现出自觉的史鉴意识
五进士编修方志共11部。观诸历史,顺治朝大部分时间忙于政权的巩固,对方志的修撰并不十分重视,直到顺治十七年才出现了第一部省编通志即由贾汉复修、沈荃纂的50卷本《河南通志》。而官方大规模倡导修志行动直到康熙十一年,由保和殿大学士卫周柞上书建议参照河南、陕西两省通志,在全国推广通志纂修并被康熙采纳。二十二年康熙命礼部檄催各省上交通志。因此结合修志时间及志序看,五进士的修志行动,大多体现出一种明显的自觉意识。
从方志文本来看,这种自觉与他们对方志的定位及其背后强烈的史鉴意识密切相关。它来自于毗陵士子对“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史书功能的自觉接受与传承,而这既是中国史学著述的治学传统在方志中的再现,也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在方志中的映射。冯达道、史树骏及徐可先正是这方面践行的典型。
冯达道在顺治十三年的《汉中府志》志序中就清晰辨析了方志的价值,即面对“户口”“赋役”“兵防”“地貌”“建置”动态的“变”的特点,志则在于“纪变也”。作者以一个高级地方官员和学者的眼界,指出了方志在服务为政者备治一方时所具备的的参考与指导价值:“备考而谨书之,使良庖司割者知大窽坚软所在,砉然游刃诊脉,而志其浮沉虚实、据案处方补泻,可以无误。志之利益如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在志序中冯达道还融合了自己十多年来对时世变化,尤其是历经战乱、民生不易的感悟,对后来继修府志者提出了“有与立计、有与定心、有与为提呼”的期望。史树骏也在《肇庆府志》志序中喊出了“盛衰之端,莫非政治”。这样的感触对于顺治初年的进士群体,绝不是一种空洞感叹,而是有着深刻的人生体验与现实的兴衰警示。
相对于冯达道等,徐可先的这种自觉意识更为明显。他在顺治十二年《龙泉县志》自序中,首先回忆了初到任时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景象,并与旧志中记载的繁华安定形成强烈比照,进而指出“读是志者,取旧新以考互,俯仰曩今,低徊兴废固知”。在调任登州知府后,“涖登逾月,輙询旧志”,在所修的府志自序中开篇即称:“善为治者,在审其急而先图焉,能裨军国则为之,能益民生则为之”,并结合当时的一统大业及登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指明方志所具有的“俾当事有所取鉴”、“援昔证今”的特殊价值。在其所作《招远县志》志序中史鉴意识更趋明显:“求所以、示褒讥、昭美剌,惟邑乘是赖,则纂修之役,乌容不汲汲欤?”。及至康熙十七年主修《河间府志》则更明确地在志序中强调志的价值:“志其地、志其地所生之人、志其地所贡之赋、志其人与地所被之政治”,并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指出“政治得失,后之志今,如今之志昔,伊可怀哉,洵可畏也”。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史鉴自觉意识并不仅仅来源于史学及儒教传统,还与科举有着关联。科举取士至明清时已趋完善,进士更是科举人才中的佼佼者,尤其进士乃是经殿试考定,而殿试则是联系实务与时势开考制策,又称“时务策”,它较好的体现了举子对儒家经义的融通能力以及面对实际的经世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方志的定位认识,及其在编修中的实际体现,也是对进士能力综合检视的延伸。
2.方志编修之中体现出精到的实务认知
五进士不仅对方志的定位中体现出自觉的史鉴意识,而且在具体的编修实务方面,也都有着精到的认知和总结。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志书体例的设计上,还体现在对修志难易的深刻认识以及修志人员的精心选聘上。
就体例设计而言,五进士颇费苦心。冯达道所修《新修河东运司志》虽名为运司志,但却体例完备,全书十卷,旁搜广辑,卷一为图考、建置、星野、山川、城池、盐池、渠堰,卷二为盐法,卷三为制救、监临、职官、宦迹,卷四则为学校、师儒、选举、秩祀、风俗、武备、灾祥,卷五为帝王、名贤一,卷六为名贤二、阔德、流寓,卷七为疏议,卷八、卷九为文苑一,卷十为诗赋,除前三卷直接与河运、盐业有关,其余则可以视为对当时社会风貌的广泛记录,同时还附图七幅,可谓是对运城叙论最为详尽的一部志书;而其编修的《汉中府志》,康熙二十八年汉中知府滕天绶重修府志时尽管评价冯志“篇章虽云典雅,而搜罗未免简略”,但滕氏在编纂体例上却是“仍旧志之条目,缀后来之考订”,可见其体例设计的合理。季芷在《任县志》“凡例”中首先提出:“志当分品类,视其重轻以为先后”、“其间节目又以类相从”,而从其对条目排序的阐述中可以窥见严谨的逻辑顺序;而在“官师志”中对续增的人物事迹,则注重对碑碣资料的使用且宁缺毋滥,同时在“人物志”中坚持入选之人“品必协乎公好,论比洽乎舆情”,“不能曲徇揄扬以秽信史”,也即是强调人物事迹的实证性、人物品评的客观性。如此种种,皆为的见。徐可先参修的《招远县志》在其凡例中则明示:“凡引古必载出某书,以见考据”、“宦迹、人物,必考诸国史,据其家乘,参以公议,示有征兼论定也。若见在者,恐涉贡谀,概不敢赞一辞”,这实际是对方志编修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但也更大程度地确保了方志内容的可靠性与可检索性。史树骏曾在肇庆本地人梁应时处得到崇祯版府志并借阅,后在康熙十七年编修府志时对崇祯版旧志体例提出了批评:“大约鏊之成书喜为标目,有表、有传、有纪、有志,议论虽多,考核未尽,事多舛互,编次失伦。所收艺文半于卷帙,未免滥觞之议”,这就提出了方志编修中的“如实记述”、“详尽考核”与“评点议论”间如何科学取舍、合理平衡的命题。而所有方志中设立的诸如“孝友”、“选举”、“乡贤”、“节义”等条目,则更具有典型的价值传导特征。
相对于体例优化设计,冯达道与季芷还从理论的层面对修志的诸多挑战进行了总结。冯达道在《新修河东运司志》中提出修志有“三易”、“四难”,“三易”包括“天子不称制以断,宰执不秉笔以裁,挠掣无人,注涂在我,一易也;地迩则边幅,有所必循,职专而搜讨,不容旁猎,条例显设,编摩夙成,二易也;营私无斗米之乞,畏咎无百口之忧,参考传闻,使垂实录,三易也”,“四难”则为“敬慎之难”、“详核之难”、“审定之难”、“裁制之难”。次年,季芷在《任县志》自序中则从五个方面,即文献的征集、学识的优劣、资金的筹集、文字的表达、评价的客观,既生动又具体地阐述了方志编修的“五难”。二人所述,皆为要领,且为的见。
与清代中后期修志略有差异的是,五进士在纂修人员的选择上除在职官员外,缙绅生员的选择往往别具意味,既有对其史才见识切合修志需要的考虑,更似有借助修志这一文化工程,从心理上消弭汉族缙绅对异族统治抵触情绪的努力,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顺治朝方志的编修中。典型的如顺治十六年吴守寀主持《杞县志》编修,编修人员何彝光,字叔献,康熙二十五年选贡,康熙三十二年曾再次参与县志编修。其兄何印光乃明末举人,却在北京投奔了李自成起义军;弟弟何胤光,崇祯癸未馆选的36名庶吉士之一,李自成攻陷北京被俘,复仕大顺政权,故被清代史家计六奇、谈迁分别于《明季北略》卷22、《国榷》卷100中列入“从逆诸臣”或“降臣”。但作为这样一个家庭中的一员,何彝光却被吴守寀邀请加入方志编修,且在该志人物志、艺文志中收有其家族成员的传记及艺文作品多篇。
通过对五进士所修方志的仔细研读,联系当今方志编纂中出现或面临的诸多问题及挑战,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1.继续坚持方志的史籍地位,重新彰显方志的史鉴价值
当今修志,往往注重历史事件或事实的简洁陈述,条目设置也相对简单,但缺乏内在的逻辑延伸与支撑,以及积极必要的价值传导,整个方志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单纯性档案记录特征,从而忽略了方志应有的为当下、为后人提供历史“批判性理解与借鉴”的功能。因此,从方志编修初衷及价值理念传达的角度,我们要向前人求智慧。
2.结合方志编修具体实务,积极促进史述史鉴的有机融合
冯达道、季芷对于方志编修难易的精到阐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社会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今人修志所拥有的便利条件与古人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因此,当今修志更需要在具体实务中努力做好资金的稳妥安排、人员的精心选聘、体例的科学设计以及材料的海量选审、行文的恰当表达,而对于后者,更应当努力坚持和追求“崇实、精审、文畅、扬善”的原则。
参 考:
[1]王新命、薛柱斗统修《江南通志》卷四十四“人物?皇清”,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2]清王其淦、吴康寿修《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二“人物?宦绩?国朝”,清光绪五年刻本。
[3]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6册进士冯钟岱会试朱卷“履历”之“六世祖达道”,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1月印行。
[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宫内阁大库档案119562-001、104053-001、089364-001、089099-001、086690-001。
[5]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32册卷206《诰授中宪大夫直隶河间府知府升山东提督学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级梅溪徐府君墓志铭》,清代传记丛刊158册综录类07,台湾明文书局1985版。
[6]《清圣祖实录》卷30“康熙八年秋七月。壬辰朔”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
[7]李周望纂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大清顺治四年进士题名碑录丁亥科》,《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三册“大清顺治四年进士题名碑录丁亥科”,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清光绪三十年本《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1969年12月第1版。
[8]滕天绶、严如熤辑《汉南续修郡志》卷一“旧志序”所录顺治丙申萸饮之日冯达道所撰《汉南府志序》、康熙己巳九月滕天绶所作府志序,国家图书馆藏民国13~14年翻刻嘉庆十八年刊本。
[9]冯达道修、张应征续修《新修河东运司志》卷一“序”,康熙十一年刻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0]季芷修《任县志》,国家图书馆馆藏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刻版康熙间增刻本。
[11]卢思诚、冯寿镜修《江阴县志》卷14“选举?甲科”,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四年刻本。
[12]《杞县志》(12册24卷)卷9“职官志?国朝?吴守寀”,国家图书馆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13]苏遇龙修《龙泉县志》,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12]徐可先修《河间府志》,国家图书馆康熙十七年刻本。
[13]张作砺修《招远县志》,国家图书馆顺治十七年刻本。
[14]任璿修《登州府志》,国家图书馆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15]屠英修《肇庆府志》,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二年重刻道光十三年刻本。
[16]史致卓等修《常州史氏族谱?九溪公二分》,光绪十九年常州东门德馨祠板。
[17]尹继善统修《江南通志》,国家图书馆乾隆元年刻本。
[18]马元、释真朴撰修《曹溪通志》,康熙十一年刻本,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
[19]郝玉麟统修《广东通志》卷29“职官?国朝?肇庆知府”,国家图书馆雍正九年刻本。